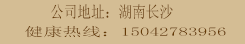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内容 > 范健资本泛滥时期的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
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内容 > 范健资本泛滥时期的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

![]() 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内容 > 范健资本泛滥时期的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
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内容 > 范健资本泛滥时期的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
作者简介:范健,南京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内容摘要:防范中国金融风险的制度路径是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并重。公司治理是本,金融监管是标,只有在完善公司治理基础之上加强金融监管才能实现标本兼治。资本泛滥时期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是公司本质的异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路径。中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应该是回归公司的本质。实现中国公司治理和金融监管法治目标,首先需要按照现代商法的理念完善我国现行公司法,构建中国公司治理的制度体系,同时需要按照现代商法理念构建商事金融基本法。只有这样,公司的健康成长和金融的正当监管才有基本的法律标准和行为依据。
关键词:资本泛滥;金融风险;公司治理;金融监管
目次
一、导语:探寻中国金融健康发展的制度路径
二、资本泛滥下的金融风险与公司异化
三、维护主体地位的公司治理是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的根本路径
四、金融监管的目标:回归公司的本质
五、结语
一、导语:探寻中国金融健康发展的制度路径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金融改革始终处于经济改革的核心地位,金融风险始终处于改革风险的至高点,金融安全始终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改革越深入,金融矛盾越突出,金融不仅仅直接影响改革的成败,更维系着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安全。探寻我国金融健康发展的制度路径,已经是处在历史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系统工程。
所谓制度路径,是指我们金融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所建立的一整套制度的着眼点、重点、方法和途径。制度路径正确,可以标本兼治;制度路径错位,只治标,不治本,并且治理成本奇高,治理效果相左。
我们一直认为,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可以消除金融风险。二十多年来,在金融改革和创新上,我们不可谓走得不远,所做的努力不可谓不多,提出的改革和创新理念也不可谓不新,但是取得的成效并不乐观。金融创新伴生了大量的金融投机,金融投机者利用公司资本构建金融产品获得了巨大的非正当利益,搅出了巨大的金融泡沫,实体产业在金融创新中获得发展的机会并不普遍,绝大多数实体企业的金融生存状态越来越差。金融创新的结果偏离了金融创新的初衷、目标和本质。相反,伴随着一系列金融创新,我国金融风险已经进入全方位暴发期,不仅仅证券、银行,而且信托、基金、期货、保险、电商、融资租赁等等,几乎各个与金融业相关的领域都开始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系列金融大案,其案情和所涉规模令人惊愕。
面对金融风险,主流观点归咎于监管不力,冀望金融监管消除金融风险。但是,仔细考量,我们不难发现,从全世界角度来看,中国的金融监管不可谓不严:我国制定了大量的金融监管、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我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队伍,组建了大量的监管机构,包括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构建了体系严密的政府金融监管机关,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层级都有金融办,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金融管理的行政系统,配备有如此众多的金融管理人员;我国也花费了全世界最多的监管费用。但其结果,我国金融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监管企求的目标相去甚远。为什么没能达到监管的最佳效果?是监管失灵,还是治理商事金融的制度路径出了问题?
商事行为,尤其金融商事行为,主要依赖商人自律还是政府监管一直是现代国家商法争议的问题。在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受到宪法的限权,尤其商主体自主权在法律上获得较高的保护,商事监管与商事自律的关系在法律上比较清晰:以主体自律为主,以政府监管为辅。传统市场经济国家商事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商主体不仅在法律上定位清晰,而且已经存在于社会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在主体意识、主体观念、主体行为、主体社会认同等各方面都相对成熟。进入现代资本与金融时代,虽然出现过主体的变异,但经历了无以计数的以社会动荡为代价的历史的教训,商主体的社会定位和自我意识成熟度较高,自我纠偏能力较强。相比之下,我国社会是一个缺乏商人传统和商法传统的社会,商人精神极不发达,进而导致商人自律精神极弱。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放权给商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一定程度上说,允许普通百姓从事经商营利活动,还只是近四十年来的一种阶段性制度设置。国有经济组织参与商事活动,也只是整个国家治理活动的一个部分。中国缺乏完整的商人制度,更没有商人精神。这种背景下,自然形成的商事重心倾向于监管,依赖于监管放权。
将权力交给监管,将全部的商事行为交由监管安排,建立在监管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过去没有成功的先例。传统社会以生产为主的商事利润来自于实业,即农产品生产和工业品生产;以贸易和服务为主的商事利润来源于物的流通和提供消费服务,商事利润的多少取决于物的紧缺程度和使用价值,服务利润的多少取决于服务的质量和需求程度。现代资本制下的金融产品,建立在商人的公司化,确切说建立在商事公司人格资本化基础之上,金融产品商事利润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资本信用评级和获取融资机会的特权。评级的特权和授予融资机会的特权与被资本化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是资本异化并导致金融异化的主要方式。是用特权来限制滥用特权,还是回归公司本质,用市场公平竞争来消除产生特权的土壤,用防范公司异化来消除公司资本的异化,这是治理金融风险的路径选择。在这一路径选择中,我们首先应该依赖制定商事基本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商事金融基本法和修订完善公司法,借助市场建立主体内在的健康机制,建立主体及其行为的自律机制,其次才是通过制定金融监管法依赖政府建立更加强大的监管机制,建立主体及其行为的他律机制。不同的制度路径抉择会导致立法和执法的差异,会形成社会金融行为的不同导向。由此,面对泛滥的金融资本的冲击,我们应该理性回归到正常公司制度中去,从现行公司制度缺陷中探寻金融风险的根本性诱因,通过培育公司的健康机体去抵御金融的有害病菌。
二、资本泛滥下的金融风险与公司异化
(一)“欧亚农业”神话的破产:资本泛滥历史教训的简单重现
公司制度的出现是人类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商事活动的主体自此开始由自然人主导过渡到以公司为代表的组织体主导。个体的联合催生了巨大的商业能量,世界生产力的面貌也因此焕然一新。西方经济学家如此推崇:“股东有限责任制的法人公司的出现是现代社会最了不起的发明,没有它的话,即便人类发明了蒸汽机和电,生产力也不会有革命性的进步。”
金融市场的繁荣则为公司插上了起飞的双翼,来自资本市场的资金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古语有云:“过犹不及”,资本同样如此。资本泛滥对公司发展乃至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亦日益凸显。章乃器先生在阐述金融含义时曾说过:“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而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但有时信用之火烧得太猛烈了,融化的金沸腾洋溢,反而要浇灭了信用之火。”资本泛滥的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新世纪之初发生的“欧亚农业造假事件”就是资本泛滥的一个典型案例。年7月,欧亚农业头顶“中国现代农业”的光环登陆香港证券市场,该公司鼓吹了一个以高科技农业题材带来高成长的美妙概念,迅速在资本市场“受宠”,获得公众投资者78倍超额认购倍数,最终募集6.14亿港元。同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欧亚农业评为全球最佳家小型公司之一,一时风光无限。但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在次年就被曝出财务造假。根据相关文件显示,欧亚农业报称公司年至年的总收入为21亿元人民币,但根据国家税务局的调查,连同该公司董事局主席的私人企业(未上市部分)总收入都不足1亿元。最终,4年5月10日,香港高等法院对欧亚农业颁布清盘令。5月20日,欧亚农业被取消上市。其董事长杨斌也因涉嫌伪造金融票据及行贿非法占用农地,被判18年有期徒刑。
然而“欧亚农业”神话的破产仅仅是冰山一角。自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市场重建以来,资本泛滥引起的虚假层出不穷并愈演愈烈,只不过手段越来越高明和隐蔽,发现和揭露越来越困难。由于资本投机获利更大更快,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抛弃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走上概念炒作,甚至造假的道路,并以此抬升股价获利;资本市场的投资人越来越“投机化”,资本市场越来越沦为投机的“赌博场”,越来越与为公司融资的“初心”渐行渐远。西方资本市场早期、中期、近期和当代引发金融风暴和经济动荡的一系列丑恶行为以极其简单的方式在当下中国获得了重演的机会,我们走近了重蹈历史金融风险覆辙的陷阱。
(二)经营重心的扭曲:资本泛滥时期的公司“异化”
公司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商业组织形态,早在14和15世纪,意大利的公司就因为其良好的商业组织系统控制了东至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西至伦敦和布鲁日的整个地区的贸易。相比单打独斗的个人,公司这一组织体拥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贸易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变革,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也得以建立。
为解决公司融资难题诞生的证券交易制度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繁荣为众多起步阶段的公司解决了发展融资的难题。苹果公司、Facebook以及国内的阿里巴巴、腾讯等大批优秀企业在发展中均不同程度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助力。近年来,资本市场迅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社会融资规模已经达到12,亿元,并且连续三年以超过50%的速度迅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在资本洪流的冲击下众多公司却日益背离了制度的初衷,开始抛弃传统的生产和贸易,转而将公司重心转移至如何更好地融资以及通过短期操作提升股价获得利润。证券违规屡禁不止,“割韭菜”成为大众调侃的对象,众多公司的经营开始产生了“异化”。
1.为了揭示公司的异化,首先需要清晰公司经营的历史演进。公司是商业发展的产物,伴随着商业发展阶段的变革,公司的经营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贸易为核心的经营。以商品和货物为交易对象的贸易活动是商业发展的早期形态。自人类社会诞生起,贸易就已经存在,社会生产的富余使得贸易有了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并催生了以贸易为职业的商人阶层。至古罗马时期,海上贸易和远距离货物运输的商业交易就已经大量存在。尽管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商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贸易一直是商业的核心。我国同样如此,古代一直存在士农工商的划分,《春秋·公羊传》按照不同的职业分工将社会民众分为四类:“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谷曰农;三曰巧心劳手人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财鬻货曰商。”此时商业与生产是完全分离的状态,仅仅指贸易环节。
从公司的起源来看,早期的类似现代公司的组织也是以贸易为经营核心的。中世纪出现的类似合伙的组织“康曼达”就是为适应航海贸易出现的。到了大航海时代,荷兰、英国出现了专门为海航贸易设立的“公司”。在商人行会获得特许状之后,由几个商人出资成立“联合股份公司”,租一条船出海从事贸易,待航程结束将赚得的钱分光,公司即宣布解散。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贸易的现实需求催生了公司这一组织体的诞生。
第二阶段:贸易与生产并重的经营。以贸易为核心的传统商业与从事生产的手工业原本是泾渭分明的,手工业者也有自己独立的同业行会。[8]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二者逐步融合,商业的内涵也得以扩张至生产领域。在14、15世纪,西方社会和中国手工业都出现过进一步扩张的趋势,直接贩售自己生产的产品成为他们的常态,手工业者走向了商人的道路,生产由“购、产、销”组成,交易成为手工业的起点和终点。但是近代成文商法的代表——法国《商法典》和德国《商法典》却一致将农业、林业、渔业、矿业等传统行业贩卖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交易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外,甚至有法国学者主张生产产品的行为全部不属于商事行为。不过,上述国家很快就意识到将农业、林业等生产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外不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所以他们后来修改了规定,使农业、林业等从业者的行为纳入商事行为之中,因此,直到20世纪,商事行为才真正包含所有生产环节的交易。
商业内涵的扩张使得公司这一组织体产生了全新的应用领域,公司经营也由传统贸易走向贸易与生产并重,并成为生产领域重要的组织形式。
第三阶段:贸易、生产与资本融合的经营。随着公司经营在生产和贸易领域的展开,公司发展的融资问题也开始日益引起北京白癜风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夏季白癜风
转载请注明:http://www.deudeguo.com/jynr/180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