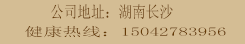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内容 > 制造业的转移,国运的轮回
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内容 > 制造业的转移,国运的轮回

![]() 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内容 > 制造业的转移,国运的轮回
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内容 > 制造业的转移,国运的轮回
1
公元年左右,元朝元贞年间,一艘海船开进了海南崖州水南村西边的港口。
城西广度寺里的一位女冠听说了有外面的海船过来,心里忽然一动。
自从十四五岁从老家松江府乌泥泾辗转流落至崖州,她已四十年没回过家乡。
如今海风既起,秋雁齐飞,似乎也该到了归去故乡的时候。
后来陶宗仪撰写的《南村辍耕录》里,记载了这位女冠的返乡:
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杆弹纺织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内外,悉习其事矣。很多年后,从崖州将搅车、椎弓和三锭脚踏纺车带到松江的黄道婆,将被当地人建祠祭祀,供为“织女星”、“先棉神”。
而她的故乡松江府,则会成为全国的纺织业中心。
松江府所出产的松江布,从明朝隆庆开关后,一直到清朝鸦片战争之前,都在国际市场上一骑绝尘,为中国吸纳来自全世界的贵金属。
西班牙和葡萄牙从土著手里抢来的白银,大半通过贸易流入了中国,换回了棉布、丝绸、茶叶和大黄。
同一时期的英国人,此时正在努力逼迫国内的自耕农破产,让他们把耕地交出来,变成草场,拿来养羊。
在公元年的英国,光是羊毛一项,就占据了全国贸易出口总额的93%,一艘艘满载羊毛的船从英国港口出发,途经佛兰德,流向欧陆。
很多年后,英国将会发展起自己的棉纺织业,此时为了养羊而发起的圈地运动,将为棉纺织厂提供最好的工人来源。
但此时,无论是英国还是整个欧洲,都还没有棉纺织业。
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棉花和棉制品就曾传入过欧洲,但是以欧洲的气候和维度,适合种棉花的地方实在是有限,也就是在意大利北部还有一些棉花产业。
在大多数普通欧洲人的认知里,棉花就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绵羊”,说不定夜里还会低头偷偷喝水。
欧洲固然缺乏种植棉花的地理环境,但两百多年后的三角贸易,又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故事是从公元年初开始的。
那一年,拿到葡萄牙王室赞助的迪亚士船队,抵达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
四年后,哥伦布带着他用西班牙王室的风险投资组建的舰队,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
欧洲和非洲、美洲相继贯通。
三角贸易的三个角,已经齐备了。
商船会从欧洲出发,载着枪支和钢铁前往非洲,在那里从当地酋长手中,把满船货物变成满船的黑奴;
接着行经大西洋,到达美洲,用黑奴在美洲殖民地的种植园里换回包括棉花在内的各种农产品;
最后再把这些原材料带回欧洲,贩卖给工厂主。
三角贸易本身具有自循环的能力,奴隶商人和酋长会用枪和钢铁武装自己,抓来更多的奴隶;
而更多的奴隶,又会在种植园里种下和采摘更多的烟草和棉花。
来自印度的棉花种子,被来自非洲的奴隶在美洲的种植园里种植和采摘,最后被欧洲的工人在工厂里纺成纱。
就如同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里所说的一样:
帝国扩张、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棉花,是资本的财富钥匙。
也是黑人的不幸。
然而,即使欧洲的纺织业已经动用了奴隶制,依然无法在和中国的棉布贸易中取得优势。
古代中国的棉纺织业,已经把小农经济下的手工业水准发展到了巅峰。
明朝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
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当时又有谚语,“松江棉布,衣被天下”,和宋朝的“苏湖熟,天下足”一样,都是以数地之力,支撑起全国市场的需求。
从黄道婆开始的松江棉纺织业,往单一技能树上加点五百年的成果,就是在技术被彻底拉开代差之前,全世界无人能敌。
据统计,到了清咸丰年间,仅松江一地的产量,就足以供应全国三分之二的布料市场。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倾销:
松江府对国内其他地区棉纺织业的倾销。
但是在有大一统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以全国内需供养松江,松江赋税同样会被用于西北。
至少,肉烂在了锅里。
另一边,面对铁板一块的中国市场,英国人麻了。
不过不要紧,英国的纺织品卖不进中国市场,难道还不能往葡萄牙倾销么?
在纺织业工厂主的推动下,英国与葡萄牙在公元年签订了《梅休因条约》。
条约规定,葡萄牙对来自英国的纺织品只征收15%的关税,而英国则给来自葡萄牙的葡萄酒同等的关税优惠。
英国的本土酿酒业,就这么被英国的纺织业给卖掉了。
以种植经济为核心的农场主,在初步资本化的工厂主面前显得弱不禁风,几乎没有组织起什么有效的反抗。
曾经被英国酿酒业主导的波特酒,成为了葡萄牙的瑰宝,直到今天,葡萄牙仍然是欧洲第五大葡萄酒生产国。
作为交换,葡萄牙得到了葡萄酒这个支柱产业,而英国则兵不血刃地得到了一个毫不设防的纺织品倾销市场。
以葡萄牙本土纺织业的破产为代价,英国壮大了自己的原始资本。
既然葡萄牙是英国世代相传的盟友,那么为日不落帝国的崛起流一点血,也是很正常的吧?
此时的英国,没时间为盟友的破产流多少眼泪。因为下一步,就是对中国市场的入侵。
倾销,倾销,倾销。
这个词如此轻飘飘,却又如此沉重。
据梁方仲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中的统计,中国借助在国际贸易中的顺差,获得了大量的贵金属储备:
从公元年到公元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对中国白银的输入,至少在一亿两白银以上。
这笔钱,已经让西方世界眼馋得太久、太久、太久了。
在几百年间,中国的纺织品市场一直被松江保护得很好。
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又一直被黄道婆留下的遗泽保护得很好。
直到公元年的到来。
在那一年,英国机械师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大幅提高了织布效率。
而3年后,英国兰开夏的织工哈格里夫斯又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将传统手工纺纱的效率提高了8倍。
英国人也有了自己的黄道婆。
在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普及到兰开夏的机械纺织厂里面后,英国棉布的生产成本更是被降低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
即使加上运输到中国的物流成本,仍然能做到和中国本土布料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宽则三倍”。
公元年,中国的棉纺织品贸易由出转变为入。
自从黄道婆从崖州回到松江以来的五百年间,这是来自海外的洋纱和洋布头一回打败中国本土的棉布。
倾销来了。
虽然由于瓷器和茶叶贸易的存在,中国的整体对外贸易仍然保持出超,但以松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棉布的时代,已经迎来了落幕。
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松江布一直是全世界最顶级的手工棉布。
松江没有败给兰开夏,而是败给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英国献祭掉的酿酒业,和上百万被圈在工厂里的英国棉纺织工人。
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
反之亦然。
3
就在中国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贸易逆差的时候,日不落帝国的财富正在飞快聚集。
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工业革命,把这个岛国推上了世界的王座。
绵延整个地球的海外版图和殖民地兵源,让英国在一百多年后仍然有底气说:
在流干最后一个印度人的血之前,大英帝国绝不妥协。但是另一方面,似乎不需要等到一百年后,也不需要等到印度人的血流干,英国工人的血,就已经要濒临干涸了:
工厂在吸纳就业的同时,也摧毁了原本的手工制造业,造成了手工业者的批量失业和就地进厂。
工业革命在让英国变得强大、让贵族和资本家获得财富和话语权的同时,也让底层普通人不得不被更高效地榨干。
在手工制造业的时代,熟练工是重要的资产,掌握手艺的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还需要消耗很多原材料培养手感。
但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时代,工人只需要简单培训就能上岗,生产效率由机器效率决定,一个熟练工的价值并不比一个新手高出太多。
在资本家的逻辑里,只要能逼迫工人持续工作,一天工作的时间越久,生产成本就会越低。
于是,工人变成了消耗品,一个个死在工厂里,又一个个被抬走。
等到破产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全部填进去都不够用的时候,英国议会干脆在公元年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
直接抓乞丐进厂。
据史料记载,公元年,在英国棉纺织厂二十一万九千名工人中,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占四万九千,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少年占六万六千,成年妇女占六万七千。
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
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大清早二、三、四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十一、十二点钟。
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
公元年,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
史书上的数字,从来不只是数字。
每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乃至一个个家庭。
工业化的力量如冰山般显现的同时,工业转型的阵痛也在浮出水面。
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核心燃料,是人命。
红利,红利,红是血的颜色。
这一切只有在工业生产开始自动化,摆脱了熬人力的初级阶段后,才能得到解决。
在此之前,工厂里那一台台蒸汽机驱动的巨大机器,消耗的燃料不只是煤炭,更是英国工人的血。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摸着石头过河,英国工人就是被摸的那块石头。
他们付出了代价,所以也尝到了甜头。
4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英国那场从十五世纪开始的、持续了三百年的圈地运动,到达了最高峰。
公元年到年的十年间,英国有七十多万英亩土地被圈占。
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一部分流入了城市的作坊工厂,就地转型为产业工人。
他们忍受着每天1小时甚至16小时的工作时长,无比怀念还能当农民的日子。
而另一部分,则去了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成为了种植园的农场主和走私贩子。
这是属于英国农民的“入关”。
几年后,一群走私贩子会乔装打扮成印第安人,在波士顿湾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倾入大海。
没有人知道,这些人中是否有当年从英国远走的破产农民。
不过不重要了,他们即将获得一个新的名字:
美利坚。
公元年,美洲殖民地代表在费城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国宣布建国。
失去北美这个泄压阀后,英国的国内矛盾没了出口,日不落的版图上多了一大块阴影。
而且这块阴影还挺闹心,时不时就跳出来提醒一下英国自己的存在。
就像第一次英法百年战争后,英国天天琢磨着从佛兰德偷技术一样,美国也继承了英国的传统艺能:
盗窃纺织技术。
建国十五年后,美国开国元老、首届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写了三份国事报告,分别是《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三份国事报告中,前两份报告最终在国会上通过并成为法案,但最后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却成为了汉密尔顿唯一一份没有被国会通过的报告。
对当时的美国来说,作为一个还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国,汉密尔顿对于制造业的投注力度太吓人了。
在这份报告中,汉密尔顿提出,可以实行大量措施保护美国尚处幼稚阶段的制造业,哪怕这些措施显得很流氓。
在接下来的论述里,汉密尔顿把制造业抬高到了涉及国本的地位:
“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制造业这么重要,那么我往英国派几个技术间谍,也是很正常的吧?
于是在公元年6月,一个叫弗朗西斯·洛威尔的美国人带着家人去了趟英国,顺便逛了逛曼彻斯特和兰开夏的纺织工厂。
这一“闲逛”,就是两年。
两年后的夏天,他在回国的路上被人截住,英国人觉得准能从他的行李里搜出一些纺织图纸或者零件啥的。
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弗朗西斯·洛威尔的行李箱里,没有任何与纺织技术有关的东西。
他全都记在了脑海里。
回到美国后,弗朗西斯·洛威尔迅速开办了自己的纺织厂,用的都是凭记忆复刻出来的最新的英式设备,甚至还略做了提升改进。
虽然美国工业革命的起步要比英国晚30年,但是在各行各业的“弗朗西斯·洛威尔”帮助下,美国很快就抄全了作业,补足了工业基础。
紧随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好运。
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产业的高度发达,国内的机械设备老化、而用工成本却逐渐升高,英国资本开始找接盘侠。
大量的实体产业被英国输送到了欧洲大陆和北美大陆,工业门类齐全,并且极度重视制造业发展的美国,抓住机会拿到了最大的好处。
很多当年的商业间谍和技术大盗绞尽脑汁都弄不回来的东西,被英国资本家连人带产线一起送到了美国。
但光是能把东西造出来还不够,还得有地方卖出去。
英国当年可以把商品倾销到北美和印度,美国自然也需要找到一个能承载国内溢出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市场。
有足够的市场来承受过剩的工业产能,企业才有进一步扩大生产和改进技术的动力。
这个市场最好是一个农业国,并且盛产金银。
美国选中了日本。
5
自从公元年,那四艘从美国弗吉尼亚出发,燃着浓烟、通体漆着黑色柏油的黑船叩开了日本国门后,美国和日本的不解之缘就开始了。
继英国对清朝进行的炮舰外交之后,美国也有样学样,开着军舰对日本幕府喊话:
开门,自由贸易。
但是以日本当时的生产力,除了装在稻草编织袋里的海参和鱼干,还真没什么东西能对外销售。
所谓自由贸易的结果,就是白银和黄金的单方面外流。
很快,以洋纱、洋布为代表的、来自工业国的低成本货物无可阻挡地挤占了日本市场。
倾销,倾销,又是熟悉的倾销。
手工业者大量破产,本来就发展得不怎么样的本土纺织业被冲击得一塌糊涂。
但痛苦中也隐藏着机会。
通过对外国纺织技术的山寨,日本的棉纺织业用很低的代价就实现了从0到1的工业化。
工业化是有惯性的,一旦开始,就再也无法停下来。
从公元年第一个引入蒸汽罐和蒸汽机的富冈缫丝厂开始,日本各地的工业化纺织厂遍地开花,很快就完成了从1到的复刻。
来自破产农民家庭和手工业者家庭的女工纷纷涌入缫丝厂,她们日夜两班轮岗,让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就像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国曼彻斯特和兰开夏的工厂中所发生过的一样。
日本把国运,赌在了纺织女工们的双手上。
时间来到公元年。
这是日本昭和时代的第6年,昭和风气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日本已经有了很多非常“昭和”的人。
经济学家赤松要就是其中之一。
在观察了这些年日本棉纺产业的发展情况后,他发现日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我们的工资低。
别笑。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关键性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唯一的优势。
那一年,他发表了一篇经济学文章,叫《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到了一个雁行模型理论。
按照这个理论,日本的棉纺织产业发展,是三只先后起飞的大雁。
第一只大雁,是被欧美国家倾销之下的进口浪潮。
第二只大雁,是山寨,山寨,再山寨,学会了欧美国家的技术以后,再用极低的人工成本和资源成本,生产出更便宜的本土商品。
第三只大雁,是一只复仇之雁。
来自日本的廉价纺织品占领了国际市场,开始反向挤压欧美国家的棉纺织产业。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产业资本赚取了大量外汇,这些外汇又可以买回更多的纺织机械,让日本的工厂尝试进行机械仿制和生产。
在生产纺织机械的过程中,日本培养出了自己的机械工业,顺便催熟了机械工业配套的钢铁和机电产业。
接下来的时间里,以少女为驱动力的棉纺织业自下而上推动着日本的产业结构,一步步往更高的层面发展。
当年第一批进厂的少女已经嫁为人妇,但永远会有新的年轻人进厂。
一直到赤松要发表完这篇论文的十几年后,日本的很多缫丝厂里,仍然挂着“生丝就是外汇”的标语。
标语下面站着的,是日本燃烧了几代人的鬼魂。
红利,红利,红利。
6
公元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十四年后,日本无条件投降。
筚路蓝缕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终于被日本习惯性地赌国运,给赌炸了。
久赌必输,何况日本次次梭哈。
二战结束后,日本只能靠牺牲民生维系工业的“倾斜经济”策略,才保留了一点工业火种,一直苟到了公元0年。
那一年,朝鲜战争爆发。
这一战,让中国重获国际地位,打断了美国人的亚太地区战略,也给了日本制造业第二个机会。
因为离朝鲜近,并且具备基本的工业能力,日本被美国当成了战争补给基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在日本采买了大量的工业物资。
突如其来的巨大外需犹如给半死不活的日本经济灌了三斤夜里猛,让日本的产业资本一下子支棱了起来:
光是为美国大兵修车,就拯救了战后稀烂的日本汽车制造业。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刺激下,日本制造业逐渐复苏。
与此同时,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了。
第一次产业转移,是英国到美国。
第二次,是美国到日本。
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国内自然资源和人力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资本集团开始在全球寻找成本更低、并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区域,然后把国内的工业转移过去。
工业于一个国家的战略意义当然很重要,但是当工业变得没那么赚钱,尤其是出现了其他明显赚钱更多而且更轻松的生意时,资本就会自发地找到退场的路径。
而在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对比下,工业顿时不香了。
战后重建中的日本,引起了这些资本集团的注意。
在成为第一次产业转移的接收地后,日本制造业以饕餮般的食量,疯狂引入欧美资本的重工业技术。
日本企业搞重工业的思路非常清晰,就像当年搞棉纺织工业一样:
先帮欧美厂商代工,同时山寨对方技术和设计,然后利用更低的人力成本和规模化效应,生产出更多更便宜的工业产品,反过来再卖给欧美市场。
成立于公元年的爱信精机,是丰田和美国博格华纳的合资公司,刚开始使用的是博格华纳授权的技术,但现在爱信AW生产的汽车变速器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
一切就像是公元年赤松要雁行模型理论的plus版,只是这一次,反噬西方国家的那只大雁,从布料变成了汽车,体量更大,力度更猛。
公元年,日本汽车产业体量超过意大利,达到世界第五;
公元年,超过英国,达到世界第三;
公元年,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
公元年,日本汽车产量突破一千万辆,占当时世界汽车总产量的30%以上,成为世界第一。
到了80年代初期,日本汽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0%,而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汽车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却接近0%。
美国汽车工业的后门,被日本冲了个稀烂。
这是产业转移的威力。
7
日本汽车工业的崛起,间接导致了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的衰败。
在那首说唱歌曲《Wel
转载请注明:http://www.deudeguo.com/jynr/22328.html